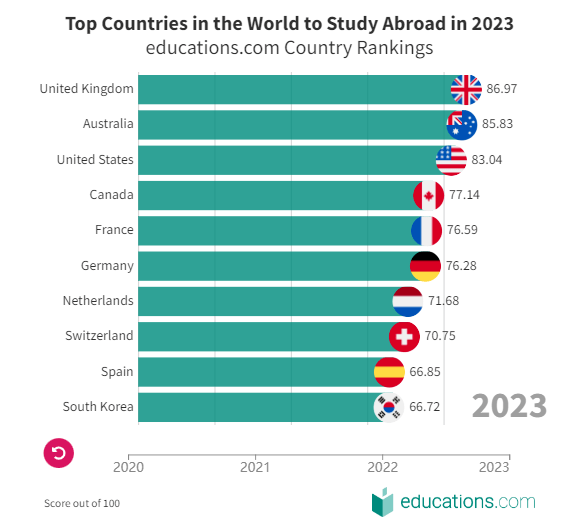约翰·让和马蒂妮一样,是我最重要的老师。一开始我就把他们当做了自己最亲近的人,所以没有在他们的名字后面加称谓。
第一次看见让,是因为上厕所的时候,发现厕所隔壁有个房间半敞着大门,里面传出来大声的争执。一个穿着老式西装,头发梳得溜光的老头,正慷慨激昂地面对着校长在分辩着什么。从厕所里走出来,校长已经离开了,而那个老头则十分沮丧地垂着脑袋坐在那里叹气,这就是让。
我有点好奇,把脑袋伸进去张望了一下,让正巧抬起无光的眼睛,对着我看了看,然后招了招手,我就进去了,坐到了让的对面。
让好像忘记了是他自己把我招呼进去的,甚至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。我坐在他的对面有点进退两难,刚刚想再溜出去,让突然开口说话:“这本犹太小姑娘的日记,你从小学开始到现在一共学过了几次?”
我不用抬起头来看就知道是《安妮日记》。记得小学五年级第一次夹带在回家作业里,后来到了十三岁那年,也就是在安妮写日记的年龄,被老师要求重读了一遍。这些天我看到刚刚发下来的“课程安排”,里面又有《安妮日记》这四个字,正有些不以为然,但是没有提出任何异议。因为我知道,在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度,可以反对任何人,甚至总统,但是不能反对犹太人,好像反对了犹太人就会变成纳粹的帮凶,就成了不得了的敌对分子了。
那时候让还不是我的任课老师,但他是我们学校的英语教研组负责人,我想让这次可以出面反对校长,要把《安妮日记》从教学大纲里拿掉的先天条件是:他本身就是一个犹太人,他是最痛恨纳粹分子的了。他从教学质量的角度提出来:一遍又一遍地重读这个十三岁的小姑娘的日记,有点浪费时间,还不如腾出时间阅读其他经典著作。
我表示赞同,让立刻高兴了起来,先是把我转入他的班里,又常常在课堂里和我对话,交换各自对文学作品的不同看法,这好像对其他同学有点不公平,但这就是美国,要学习的无止无尽,不要学习的没人管你,你可以自由自在,做自己爱做的事情。
还记得让特别向我推荐了《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》一书,这实在是一本非常枯燥的小说(?)我在这里打了一个问号是因为我不知道这是一本“小说”还是柏拉图式的“对话”。读起来相当晦涩,但那个年龄段的我,越是艰难,越是读不通,越让我感觉到高深,也就越是要去攻克的了。我花费了差不多一个星期,把这本又是“禅”又是“维修”又是“艺术”的怪异的书读了一遍。
那时候正巧是炎热的夏天,我就好像跟随着那对父子和约翰夫妇,骑着摩托车从明尼苏达,跨越美国大陆,到达了加州。因为小时候爸爸开车带我走过这段路程,更有在旷野里行驶的切身感受。那里面寻求生命的意义以及自我的解脱,透过自然的景色、野外的露营、夜深人静的谈话还有摩托车的维修和日常生活的点滴,通通流露了出来。这是科学与艺术、精神与物质的混合。全书以两个故事不断地交叉行进,一个是“我”和儿子,还有一个主角叫“斐德罗”,不断地在一边散布着抽象的理论。我后来告诉让,我注意到“斐德罗”也是柏拉图《对话录》当中的一个人物。
对不起,妈妈不喜欢这本书,特别是那个精神病兮兮的斐德罗,执着于他的抽象理论,连篇累牍地讨论着《道德经》、庞加莱、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还有“禅”等等,他在大学里教书,却处处反抗西方哲学的正统观念,活该把自己逼到分裂。最后一个场景,斐德罗盯着墙壁看了三天三夜,“他的尿液流满了房间的地板,他也不觉得讨厌和羞愧。香烟一直烧着,烫到了手指,然后手指起了水泡。”
这算是什么东西,一点也不健康,不阳光,没有美感,简直就是病态。我认为现实生活已经够丑陋了,黑暗的东西太多,我希望我的小狮子阳光,快乐,而这个让,总是推崇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给你读,让人担心。
我看过你们的中学生阅读书单,这是印在“课程安排”后面的书目里的,除了但丁、莎士比亚、塞万提斯、简·奥斯汀、托尔斯泰等等作家的作品以外,还有:
美国《大亨小传》(TheGreatGatsby)
爱尔兰JamesJoyce《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》(APortraitoftheArtistasaYoungMan)
英国AldousHuxley《美丽新世界》(BraveNewWorld)
美国JohnSteinbeck《愤怒的葡萄》(TheGrapesofWrath)
英国GeorgeOrwell《一九八四》(1984)
英国RobertGraves《我,克劳迪亚斯》(I,Claudius)
美国KurtVonnegut《五号屠场》(Slaughterhouse-Five)
英国GeorgeOrwell《动物农庄》(AnimalFarm)
英国WilliamGolding《蝇王》(LordoftheFlies)
美国ErnestHemingway《太阳照常升起》(TheSunAlsoRises)
美国WilliamFaulkner《八月之光》(LightinAugust)
美国《麦田捕手》(TheCatcherintheRye)
英国JosephConrad《黑暗之心》(HeartofDarkness)
……
这个书目还只是普通中学的阅读书目,假如和那些私立学校相比只是沧海一粟了。其中的覆盖面之广,远远不是许多中国家长想象的那么简单。难怪后来许多凭着SAT高分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,知识面明显要比美国学生窄很多。只是美国学生也不是人人优秀,这个书目的阅读规矩和以前一样,那就是“爱读不读”。有的学生毕业以后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书目,而有的学生的阅读则远远超过了这些,就好像你。
让对你视如己出,不断地给你个别指导,因此你在很早就读了《洛丽塔》(Lolita),这是俄罗斯裔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·纳博科夫在1955年发表的作品,我是到了成年以后才接触到。对此我很有些不快,我把我的想法和伊讨论,伊说:“这又不是你小时候,‘文化大革命’当中,后来就算是家教威严,你不也偷偷读了《十日谈》吗?在你现在当了妈妈的脑子里,那是更加直接的不健康了呢!你是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来读这一类的书的。相信小狮子,他会有自己的分辨能力,生活在这个环境里,这是必须的。”
但是转念一想,不对头,这里面怎么没有写清楚“主题思想、创作方法、写作结构”等等呢?这些都是我读书的时候必须要背下来的呀!你那样的写法对头不对头啊?
在让的班级里没有“对头不对头”的这一说法,只有合乎不合乎逻辑。让最不喜欢的是死记硬背,他说:“我又不是你们幼儿园里的体育老师,和你们一起丢皮球,上课的时候我把皮球丢给你们,到了考试的时候,你们再把皮球丢回给我。这样的试卷,我会打零分的。”让还说:“在我这里是没有标准答案的,我讲的只是我的想法,而我要的是你们的独立思考和创造性的见解。”
让似乎有意引导我们走上和他唱反调的“歧路”,有时候在课堂上我会和他争论,也带动了同学们的起哄,常常把他逼迫到十分尴尬的地步,他反而很高兴。为了可以和他对峙,我大量地阅读。《红字》《罪与罚》《包法利夫人》《红与黑》等等这一类的书,都是在那一段时期读的。至于圣经和希腊神话几乎是每日必读的。渐渐地,我发现自己在文学的大海里面不可自拔了。
我不知道这是件好事还是坏事,但书确实为我展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现实当中的痛苦让我沉湎于书籍,在书籍里面,我更多地思考。妈妈以为我不会面对现实,而我则以为自己看透了现实里的世界。让时常也会赠送我一些他喜欢的书,我开始藏书了。
和我的同龄人相比,我的藏书是非常丰富的,妈妈最喜欢让她的朋友来参观我的藏书,在我的卧室里,顶天立地的书架占据了三面墙壁,足有近千本书,其中最让我得意的是从上海背过来的一百多本“老书”,这是我外公的遗产。
在我第一次回中国省亲之前,我的好婆以为没有后代会再去读这些英语原版书了,于是准备捐出去。接收单位来不及高兴,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,就是我,我一把拦住,运到美国来了。我发现外公的英文藏书多数是英国伦敦“EverymanLibrary”和美国“ModernLibrary”出版的,他喜欢的是莎士比亚、丁尼生、雪莱、济慈、华兹华斯和司各特,这些书多数是精装本。让看到了说:“这些书非常珍贵,不是一般人收藏得起的。”
我告诉让:“我的外公是个写书的人。”
让立刻说:“这很不容易,你的外公是个作家,他一定读过很多书,你的爸爸妈妈都是做文学工作的,是不是你将来也要学文科?”
千万不要!父亲在世的时候,就反对我们去走他的道路,哥哥考上清华大学,让他松了一大口气,因为他很知道文学这条道路的艰难,特别是在他那个年代,弄不好就会变成“右派”。可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对文学情有独钟,我知道这里是个号称是自由的国家,但我们毕竟是外国人,别人到底是怎么想的?不知道!长期以来的禁锢,总让人心有余悸,我的小狮子啊,你千万不要闯祸呵!
这一天吃完晚饭,你很得意地把我们叫到你的房间里,从书包里抽出一张英语课上完成的作文草稿,让我们一起阅读。我不知道让为什么会想出这么一个题目:什么样的政府才是最成功的政府。
伊一读大声叫精彩,而我一看浑身冰凉。小狮子,你真是胆大包天了,你怎么可以这么说:“会骗人的政府才是最成功的政府”!接着洋洋洒洒一大篇,我不知道是讽刺还是赞赏,是正面还是反面,论点、论据、论证滴水不漏。不得了,小狮子你这是要闯祸了!
我想起来你最小的时候,被幼儿园里那个雀斑老师说成是“有思想问题”的小孩,现在真的验证了。整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是“思想问题”,弄不好把你当做“反革命”甚至是“敌对分子”抓起来。我越想越担心,半夜三更睡不着,好像又回到了当年我所经历的时代,跟在幼年的保姆胖妈的后面,在上海一家监狱的铁笼子里,看见一个个关押在那里的“反革命”,刹那间心惊肉跳,一身冷汗。
从热乎乎的被子里跳了出来,用力摇醒呼呼大睡的伊,说:“这一下要出大事了,小狮子怎么可以交出去这样一篇批评文章,明天要被警察捉进去的啊!”
“你做梦啊?”伊翻了个身又打起呼噜。
“你快点爬起来!警察来抓人了!”我歇斯底里大叫。
伊一个骨碌跳了起来,站在地板上,两只手抓住我说:“啥事体?啥事体?”
我一屁股坐到伊的被子上,不让伊再睡回去,然后就好像机关枪扫射一般,把我的担心全部释放出来。最后说:“这篇文章全部都是反面的论点,没有一点点的肯定,很不全面,就好像瞎子摸象一样。”
这一下伊真的醒过来了,伊走到我的面前,摸了摸我的额头说:“你这是发烧啦?怎么牛角尖钻到《涅槃经》里的瞎子摸象了呢?过去,我们当学生的时候,老师总是教导我们不可以瞎子摸象,要全面地分析,但在现实生活里,谁不是在瞎子摸象?可以做到瞎子摸象已经很不容易了,只要通过一只耳朵一条尾巴,把自己的感受、体验讲清楚,就是最有价值的了。”

伊讲完了,不由分说把我从他的被子上拖起来,又钻进被子,回到伊的呼噜里去了,而我是一点点睡意也没有了。趿着拖鞋,走到你的房间里,洁白的月光一如既往地洒落在你的脸庞上。我俯下身体,仔仔细细观察着你脸上每一表情,在那里没有微笑也没有痛苦,只是坦然自若地平稳呼吸着。
上帝啊,菩萨啊,神灵啊,老天爷啊,我都不知道祈求什么好了,我只祈求保佑我的小狮子,我跪了下来。
朦朦胧胧的时候,听到妈妈窸窸窣窣地跪了下来,我赶紧闭上眼睛,不让她察觉。我知道她完全是出于她自己的经验而为我担心,我不知道怎样去安慰她,也不可能去承诺把我的思想禁锢起来。我只有一个念头,那就是:“放心吧,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。”
第二天放学,远远地就看见妈妈来了。我好像有预感她会为了那篇作文,提早下班来接我一样,便把刚刚发下来的成绩单攥在手里。我从校门口的斜坡上跑了下去,那里的停车场上,妈妈把小车停在两条白线的中间,正靠在车头上和让交谈。看着她满脸春风的样子,我相信一夜的阴影已经烟消云散了,让一定在那里夸奖我,因为昨天的作文,我得到了一个A+++。
这是我在让这里第一次拿到A+++,通常都是A+,有时候他也会给我A++,而A+++好像是唯一的一次。妈妈总归会说美国人对中国人是有种族歧视的,她不会忘记小学里的“拼字Bee”,更不会忘记我被降入“慢班”的往事,但是我不都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战胜了吗?因此我以为只要自身强,别人就根本没有办法歧视你了,谁歧视你,就会变得小丑一样,歧视、讥笑了他自己。
为此,我会相当努力地读书,特别是主课英语,我是一定要拼到第一的。再想起来也是上帝爱我,我遇到了一个让。
让在这个学校里已经任课三十多年了,今天上课的时候,他突然指着自己的秃顶说:“你们知道我这里的头发都到哪里去了吗?”
因为问得唐突,喧哗的教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接着他又说:“都是送给你们啦!”
同学们哄堂大笑,又各做各的事情去了,没有人再去理会他的话。据说让本来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,大学毕业以后又回到本校来教书,和一个辅导员结婚生子,一直到现在。让的人生实在是一点意思也没有,就好像好婆弄堂口看门的工人,退休的时候,他把他坐的凳子要回去了,他说这是他坐了一辈子的凳子。
听起来有点吓人,仔细想想很可怜,这就是人,人生。不对了,我这么年轻,怎么会有这种念头?不要出毛病了。我被我自己的想法吓一跳,抬起头来,正看到妈妈对着让不断地点头,一定是被让的“说教”骗进了,让在教室里很少有听众,但在家长当中很有威信,他毕竟还是学校里的核心人物,专门分管辅导员的。
我当时并不知道辅导员有多么重要,可是到了后来,到了要申请大学的时候,辅导员的办公室门口的条凳上,就好像我小时的反思凳,天天坐满了排队的人,有学生也有家长,这些都是后话了。而现在,妈妈好像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,在其他家长的脑筋还没有转过弯来要和辅导员搞好关系的时候,妈妈已经和辅导员混得很熟了,特别是他们的“头”——让。